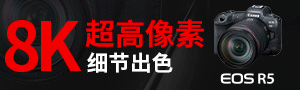/ 香港的南看台 /
图片
艺术家:秦伟
出生及成长于香港。 现任教于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当代摄影深造文凭课程。 早年毕业于法国米卢斯高等艺术学院,以当代西方的艺术造型表现和东方美学思维的结合,完成其修业研究。
秦伟认为艺术不应拘泥任何形式,而是生命的全然开放。他的创作涵盖雕塑、装置及摄影等范畴,尤重摄影,他相信摄影是探索存在与本质的路径,可从中构建思考空间。他的摄影题材严谨而富寓意,镜头聚焦于这个急速变动的时代,作品糅合文学与纪实手法,建构出隐晦的影像语言,流露着对这个时代的仿徨与期盼。曾多次获颁人权新闻奖。已出版作品包括《香港的南看台》、《时间的漫游》、《另一段的地平线》、《在天堂之下》及《板间人生》。作品获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、香港文化博物馆、法国Mulhouse市政府、阿根廷萨塔尔当代美术馆(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of Salta,Argentina)收藏。
秦伟和沈昭良二人在国际摄影活动中认识。秦与沈于年青时期分别在法国和日本留学,及后在新闻媒体担任摄影记者工作,现致力于当代影像的教育工作,并在不同的国际平台上筹划和推动摄影文化。秦和沈的作品都具个人独特性及思考性,同时二人都擅长拍摄大型且持续长时间的项目,彼此在摄影路上有着相近的历练和取向。
这篇对谈话题环绕两位摄影师的创作经验,并对秦伟的作品《香港的南看台》,从多面的角度去解读,包括摄影语言的讨论和图像背后的深度思考。
沈:想先了解一下,《香港的南看台》这组作品的构思很幽默有趣,你这个拍摄项目的原点是什么?
秦:《香港的南看台》的拍摄项目始于1995年,至今不觉已是二十多年的光景。事缘每年三、四月间香港的国际7人榄球赛,这是一年一度的体育盛事,球赛只是为期三天,却吸引不少世界各地的球迷粉丝来港观赛,场面气氛极为热闹,可称得上是成功的体育比赛活动。在球场内南看台的观众席,有个很特别的传统,球迷都悉心打扮、三五成群一本正经地演各种角色,这种插科打诨的调侃方式,让南看台变身成狂欢的舞台。我尝试在一个以开玩笑的题材上延展深层思考和探索,解构狂欢世界背后所引伸出的种种讯息。起初我打算做个小品式的拍摄方案,结果一晃便是二十多个年头。
沈:其实我在看《香港的南看台》这组作品时,发现它是蕴藏幽默和嘲讽,包括跟生活上面对的权威、性别、身体和族群的各种关系,整个幽默的范围是蛮多元和全面的,对我来讲是一种比较陌生的英式幽默。
秦:《香港的南看台》中我是作为一个旁观者,用一个抽离的态度去观看在球场内狂欢的粉丝。我通过摄影,细味及思考眼前事物的关系是什么?我又如何通过这关系去理解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。在这组作品中,我拍摄的对象都是不真实的、虚幻的,他们以另外一个身份角色去介入;对着我的镜头,板起面孔一本正经地讲鬼话,演活这个时代中的事情。
沈:这让我想起日本摄影师鬼海弘雄,他用了45年的时间在日本东京老区浅草寺附近拍摄路过的人物,一共拍了1000个人物。他为每一个被拍者拍摄一卷120胶卷,有12张,然后从当中挑出一张。他对人物的自然样态的掌握有独到的技巧,我觉得他跟你在《香港的南看台》中拍摄的人物有异曲同工的地方。你们都能够拿捏被摄人物,在经过自然沉淀之后所反射出的内在特质,拍摄带有摄影师独到的观点。
秦:谈到人像摄影,自问我不是什么高手,我对鬼海弘雄不算熟悉,但观阅他的作品时有一份宁静细腻的感觉漫延出来,很内敛,也很人性,你需要花些时间进入他的照片,找出那份厚实。鬼海弘雄也让我联想起理查德・阿维顿的《在美国西部》的肖像。他驱车前往美国不同的地方,拍摄不同阶层的人物,而他是刻意把影像的背景去掉,图像中的人物恍惚就像处在一个真空状态。
沈:我觉得你这组作品形式跟查德・阿维顿的照片是有对应的,都是以比较朴素或白色的背景,这样更能够突显被拍的主体。
秦:理查德・阿维顿是美国时装界极负盛名的摄影师,他的图片就是一种布尔乔亚美学标签,可说是不着地气,直至他拍摄《在美国西部》,似乎有种缘华过尽返璞归真的感觉。然而我并无意模仿理查德・阿维顿的拍摄手法,只是在重阅这组作品的时候,让我找到类比,与理查德.阿维顿的《在美国西部》去背景化的对口之处。
沈:你能否说明白一点,在《香港的南看台》中的你是故意去背景化?还是被现场环境逼出来的?
秦:是的,我在拍摄这项目时是很受现场条件限制,同时被拍者「当刻的身分」都是不真实的。故此在这个主题上,我以平面化效果及减除三维度的深纵感,采用去背景元素,让人物更接近现实。一般来说,纪实摄影有两项基本原则的要求,一是时间,另一是地点,二者需准确交代,但在《香港的南看台》这组图片中,地点与时间都被剔除。跨越二十多年的拍摄时间,在影像中好像没别的分别,一切好像在同一天发生。
沈:其实我对画面的比例也有关注,画面的比例是语言的一种。我很少用正方形的构图,我想了解你对正方形构图的看法。
秦:我是在80年代接触正方形构图,我花了很长时间才习惯使用正方形构图。原因是我们平时相机的观景所观看的方式都是横宽扁直,从上至下或从左至右,这都是顺理成章的视觉秩序。但当你运用正方度观察及拍摄的时候,便要小心了,须重新处理你眼前的视觉关系。在我习惯之后,我发现正方形构图的内在张力还是蛮强烈的,同时含有正方形的一种稳定感觉。
沈:我们来谈一下风格的问题。在你的作品中,你是怎样在每一个题材中去建立你的摄影语言?对我来说,风格或者是某种表现的语言,其实我很难为自己作出一个界定。但是最近这几年,当我面对一个特定选题的时候,我会思考用什么样的语言方法、什么样的影像规格去表现它是比较好,特别在我拍《舞台车》之后,我特别多去思考这个问题。我相信这是我的成长和改变。
秦:黑白的影像语言很有趣,有人喜欢大广角很随性地拍摄,也有不少朋友模仿森山大道的高反差粗微粒,展示内在的情绪波动。我也有留意到你的作品《歌手与舞台载》中的人物系列,细腻的微粒及偏低灰阶的黑白调子,传递出歌手对外围复杂世界欲言又止的凝视,我觉得这组图片的处理十分到位,照片中影像的感染力缓缓地流动。相对于《香港的南看台》这个主题,我采用中灰阶中微粒会更合适,可以引导观阅者以平静及抽离的心态进入图像。
但影像上过度依赖影像语言的风格化也有危害,过度地追求风格化是很容易把自己的创作变得形式化,结果把自己捆绑在一个闭塞状态,这亦是七、八十年代艺术家检讨现代主义,其失败的地方。
重点是我们拍摄的时候,怎样将眼前的事物投射到自身的内在世界,再通过视觉语言诠释出来。语言只是工具,你用什么工具传递出蕴藏于内在的所思所想所感受,并通过照片这媒介让对方激活出新一轮的感观经验,这才是艺术的意义。就像你所拍的作品一样,都是指向社会议题,作品背后能够带出对社会状况的思考,激发观者的反思和感受。
沈:是的,我也有同样的感受,就是要回应到我们自己要拍摄的题材去思考,到底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能够有效去回应所选的议题。但是在我们长期拍摄过程中能够被归纳出一种语法或者是风格,我觉得也不是坏事,但一定是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。而这也不是我要追求的。我曾经长时期当过摄影记者,我觉得这个经验对我日后发展的影响很大,很关键。不晓得你认为怎样?
秦:摄影让我可以站在最前线去观看社会发生的事情,让我吸收很多不同的人生经验,但对于我来说,艺术家也好,新闻记者也好,这些身份角色都不太重要,重要的是我们要对所处的这个世界及时代,保持充分的敏锐度,不惧孤单,走自已的路,每张成功的照片都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。
评委评语
严志刚
本组照展示了一群身着奇装异服的男女,站在统一的灰色水泥墙背景前,被定格于狂欢或游戏中的某一个姿态。这组作品刻意抹去时空的痕迹,也并无一个具体人物的姓名,这些淡漠的无所谓态度,让时间跨度超过20年的一个长期项目,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下午完成的流水线影棚作业。当观众因这些细腻的黑白影调引人入胜,企图解开好奇,却又会发现,这些故事里的主人公,是谁,什么身份,他们扮演着什么人,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自己?却并不能像过往传统的纪实摄影一样,从中找到明确的答案。摄影师从形式技术上极致靠拢传统纪实、时空上却有意逃离纪实摄影本质的作品,借助事件和幕后的角色们,一致合谋在那一刻灵魂出窍。